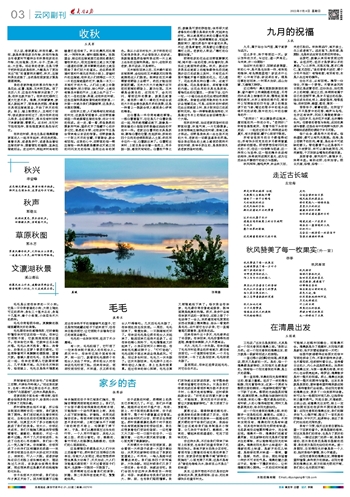苏轼曾有这样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而在我的家乡,也有一种水果让我念念不忘,我把它称作“北国荔枝”,这种水果就是杏。
老家的院子里长有一棵杏树,每年都会结很多很多的杏子,给我和小伙伴们带来了无限乐趣。
那时候物质生活不丰富,所以每当院里的满树杏花一绽放,我们就充满了期待。我们密切地关注着杏树的变化,当粉白色的杏花稍微发淡灰色的时候,比黑豆大不了多少的酸毛杏就成了我们的美食。杏太小,杏核还未成形,我们只能摘几颗连肉带核整嚼着吃,嫩嫩的、酸酸的,不过一点都不过瘾。用不了几天杏核成形,长成了白色的心形的模样,我们会一兜儿一兜儿摘下来。杏肉解馋,杏核则成了小伙伴们互相嬉戏的武器——突然将杏核里白色的汁水挤在对方的脸上,凉凉的,吓人一大跳;或者挤破涂在自己的脸上或长癣的地方,据说涂过几次后,皮肤就会变得光滑细腻,现在想来那应是最天然的纯植物的化妆品。
杏子长到半大的时候,我们的合作才真正开始了。因为树冠最下边能伸手摘到的杏子早已被我们摘光,想摘杏需要爬到较粗的树杈上。我们几个女孩子都没有很娴熟的爬树本领,只能推举一个动作灵敏的上树,其他人在下面扶着她、护着她,共同完成摘杏任务。等到半树杏被我们消灭得差不多的时候,上树已解决不了问题(细的树杈不敢上,怕踩断了掉下来),于是,我们从磨房里扛出长长的竹竿,一个人用竹竿敲杏,其他人从地上捡,然后分着吃。杏,酸酸的,拿竹竿的人的胳膊也是酸酸的,但我们的心里甜甜的。
这些事情自然都是在大人们午休之后偷着干的,那时我们总觉得自己很幸运,没被大人发现过,现在想想那种想法真是太幼稚了,天天如此,大人们怎能毫无察觉呢?只不过看到孩子们高兴,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而那棵树也任由着我们的索取、折腾,第二年照样密密地开花,繁繁地结果。
杏子成熟的时候,那棵树上的果实已所剩无几了。不过,我们并不遗憾。姥姥所在的村子盛产杏,沟底、坡上、村子里到处都是杏树,杏子成熟季节,整个村子都氤氲在杏香里。村里会给村民们分杏,即使买也很便宜。那时我最羡慕的是那个村子里的学生有到地里摘杏的劳动任务,我总在想象着他们劳动的场面:一边吃着又大又甜一咬一口甜汁的杏子,一边嬉笑着,一边热火朝天地劳动着,我心里充满了羡慕嫉妒。
不知哪天中午放学回到家里,就会看到一大布袋子或者一大篮子黄灿灿、水灵灵的新鲜的杏放在了我家的堂屋地上。不用问,一准儿是姥爷或舅舅送来的。我们姐弟四个欢呼雀跃,大快朵颐。而这时候我们又多了一项任务:给邻居、亲戚送杏吃。我们会因为杏这种水果得到另一种收获:邻居、亲戚都会夸奖我们送的杏大、鲜、甜,也夸我们聪明懂事。我们欢快地出东家进西家,似乎整条巷子都洋溢着吃杏的快乐。只是当我们彻底完成任务看到所剩为数不多的杏子时,心里不免有些懊恼,这时候我妈就会说:“好吃的东西要大家分着吃,不能独享,更何况杏不好存放,要让大家趁着新鲜吃。”我又受到了分享教育。
夏季过去,碧绿鲜嫩的酸毛杏、金黄美味的成熟杏都成了历史,但我们依然享用着杏的美味——姥姥会把夏天晒的杏干给我们送过来,我妈会隔三岔五地给我们姐弟制造点小惊喜,分几块杏干给我们,酸酸的、爽爽的,嚼起来筋筋道道的,吃完了回味无穷。
杏这种水果,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味觉上的享受,也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快乐。我离开家乡后很少买杏吃,看到市场上摆着的没有光泽的养熟了的杏,卖家居然扯着嗓子喊“新鲜的!现摘的”,心里充满了不屑,这是不是有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味道?
其实,让我怀想的不仅仅是杏这种美味的水果,更是那简单、自由、无比幸福快乐的童年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