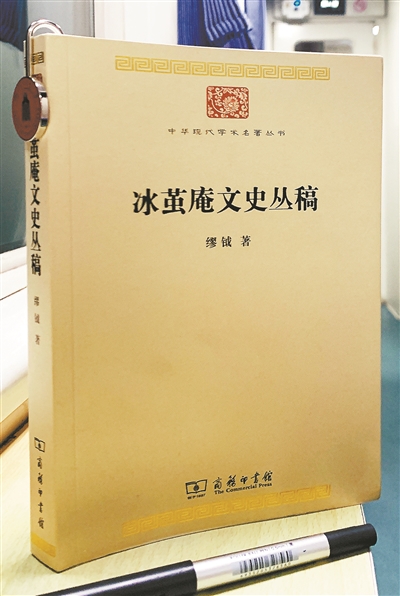杨刚
拓跋鲜卑走出大兴安岭一路迁移,都城先后从盛乐到平城再到洛阳,建立北魏帝国,统一了中国北方,踏上了华夏化道路,孕育了隋唐文化,留给后人的诸多历史财富中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这样一个历史贡献巨大的民族,在奔赴中原文化的过程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语、用汉字,有人禁不住要问,拓跋鲜卑有文字吗?
首先要说的是,鲜卑人有自己的语言。鲜卑语言在中国史书中称为夷言、国语、北语、胡语、胡言等。一般认为,鲜卑语和源自东胡的柔然、契丹、蒙古的语言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鲜卑语的使用时间大致是2世纪到7世纪中叶,一度在中国北方成为仅次于汉语或者超越汉语的权威性语言。北魏中后期孝文帝和冯太后下令进行汉化改革后,改用汉语代替鲜卑语,禁止入主中原的鲜卑人使用鲜卑语,鲜卑语的生存空间大幅度缩小。
关于鲜卑文字,历来学术界多有争论。有人认为鲜卑人有语言无文字,持此论者甚众;也有人认为鲜卑人的语言和文字都在历史上存在过,例如清人陈毅和当代学者缪钺、林幹、周伟洲、逯耀东等先生。
清代即有一些学者注意到拓跋鲜卑的文字创制问题。陈毅在其《魏书官氏志疏证》中推测,鲜卑文字应当是拓跋鲜卑借用汉字创制的。再往上追溯,《隋书·经籍志》中提到有关鲜卑语的典籍有《国语》十五卷、《鲜卑语》五卷、《国语物名》四卷、《国语真歌》十卷、《国语杂物名》三卷、《国语十八传》一卷、《国语御歌》十一卷等。由此学术界推断,鲜卑语并不是不留痕迹的语言,同时应是书写符号。
著名文史专家缪钺先生(1904—1995)是陈寅恪先生私淑弟子,斋名冰茧庵。“冰茧”取自《拾遗记》,“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冰茧”为斋名即自励“奇情寄壮采,抗节期贞坚”(先生《古意》诗句)。缪钺先生从1948年开始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研究以历史为主业兼顾文学及其他。20世纪80年代,与南开大学叶嘉莹先生共同完成了专著《灵谿词说》以及续编《词学古今谈》,以其对词史词人词心的多方面阐发和新颖别致的写作方式获得学界和读者赞扬。
《冰茧庵文史丛稿》为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图书之一。图书荟萃了缪钺先生的经典论文,如《〈诗〉三百篇纂辑考》《〈吕氏春秋〉撰著考》《陈寿评传》《论词》《论李义山诗》《论宋诗》《论李清照词》等,还有其魏晋史研究方面的力作《清谈与魏晋政治》《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等。《北朝之鲜卑语》更是一篇研究鲜卑语的宏文,发表早、影响范围大。
缪钺先生在《北朝之鲜卑语》中说,“自西晋灭亡,迄于隋兴,二百六十余年,中国北方为异族所侵据。诸异族中,鲜卑尤炽。”“鲜卑与汉人之斗争与融合,为两晋南北朝之要事,对于中国中古期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关涉甚也。”
鲜卑族的华夏化是一个过程,语言文字的演变也有个过程。“北魏之初定中原,其本族人皆操鲜卑语而不学汉语。”《隋书·经籍志》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这里的夷语就是鲜卑语。缪钺先生说,“北魏初年,鲜卑语成为一种有政治性之语言,其势力之大,可以想见。当时朝官,多用鲜卑人,盖鲜卑人熟谙鲜卑语,在政治上始能无言语之隔阂。”当时的政府部门还有一种充任翻译的官员叫“译令史”。随着孝文帝改革的进行,鲜卑语逐渐失去应用空间。
任何一种文字的形成都有个过程。《魏书》记载,拓跋鲜卑早期有语言但没有记载语言的文字符号。“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随着向汉族文化区发展,拓跋鲜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上均有了新的举措,包括语言文字方面。缪钺先生根据北魏始光二年(425)造千余新字、另有编纂《众文经》活动等文献,推论拓跋鲜卑应有独属本族的且在形态与汉字有异的鲜卑文字。
《魏书》记载,始光二年“庚申,营故东宫为万寿宫,起永安、安乐二殿,临望观,九华堂。初造新字千余,诏曰:‘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后人对于这次所造“新字”,看法不尽相同,有人认为就是整理汉字,清代学者陈毅则认为是创制鲜卑字,如同女真人创制女真文字。
缪钺先生说,陈毅则谓此次所造新字乃鲜卑字,如金人所制之女真字。然寻绎诏书,仅言“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语意含混,未敢遽定所造者为鲜卑字,陈氏之说,尚待商榷。此外,现存文献中,更无魏人造鲜卑字之记载,故吾人虽知北魏有鲜卑字,而鲜卑字造于何时已不可考,至于鲜卑字为何种形式,更无从探寻。
很显然,缪钺先生在理论上是认为历史上存在过鲜卑字的。他说,“《隋书·经籍志》所著录鲜卑语之书均早已亡佚,现存文献亦未有记录鲜卑字之资料,魏、齐、周三朝石刻保存者虽尚多,亦未见有刻鲜卑文者,自非异日有机会发见鲜卑文石刻,吾人将永不能知此鲜卑民族入据中夏时所创造之文字为如何之形式矣。”
著名学者周伟洲先生、林幹先生等为代表的学者,承袭缪钺先生之说,均认为拓跋鲜卑和后世的蒙古人、满洲人一样,不仅拥有自己的语言而且创制了自己的文字。
台湾学者逯耀东先生、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先生等也认为拓跋鲜卑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川本芳昭先生还用更为宏观的东亚视角分析说,汉唐间,处于中国边缘的族群和国家在汉文化的长期作用下出现了民族自觉意识,并创制了属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例如古代日本、古代朝鲜都根据汉字创制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由此推之,拓跋鲜卑也应该在相似的历史形势下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
缪钺先生在《冰茧庵文史丛稿》一书中说,“自隋室代周,鲜卑人与汉人同化,鲜卑语亦渐趋消歇。”今天有学者进一步研究认为,拓跋鲜卑假借汉字创制了鲜卑文字,在民族融合的高速进程作用下,唐代人们就无法一窥鲜卑文字的全貌了。鲜卑文字的使用时间上限应为北魏初年创制文字之时,下限则不迟于周隋;另外,鲜卑文字使用范围仅集中于少数精英人群,而非全社会。如是,鲜卑文字存世不长就成了死亡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