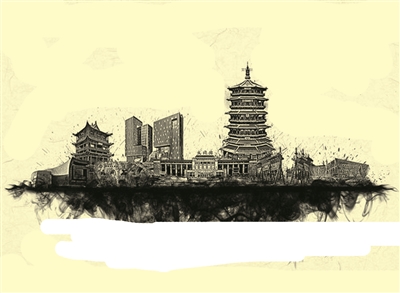谜一样的历史,谜一样的故事,连昙媚本人恐怕也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她留下的造像题刻,会成为后世眼中的“魏碑神品”,引人长久观瞻。
北魏景明四年(公元503年)早春,平城(今大同)西武周山下,和风轻拂,嫩草探头,春天的温暖扑面而来。当武周山石窟寺的香火袅袅升起时,僧人们低沉而悠远的诵经声,回响在武州川两岸。
一位法号“昙媚”的比丘尼,身着常服,手持念珠,步履匆匆地出入于石窟寺各洞窟间,像是在寻觅什么,又像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游览。石窟寺的僧人们经常会见到这位心境澄澈的出家人,听说她想选择最佳的洞窟开龛造像,便在心里祈愿她诸事顺利。昙媚看到众人投来慈悲的目光,虽心领神会,却总是沉默寡言。法号中一个“媚”字,似乎说明这位比丘尼凡心未泯,但从她静穆又平和的容颜中,又能看出她一心向佛的虔诚。
就是这位法号“昙媚”的比丘尼,于北魏景明四年的春天,在武周山石窟寺开龛造像,给后世留下了精彩,也留下了许多千古难解之谜。
出家人本该永诀红尘,不染杂念,但俗世社会的更迭与纷争,身处平城的昙媚多少都有耳闻。然而,自打北魏迁都洛阳后,武周山下开凿石窟的鼎沸声,似乎一下子成了往事,而洛阳伊水之畔的香山和龙门山,却成了北魏王朝礼佛崇佛的又一圣地。春天的风吹来,武周川荡起阵阵涟漪,没有人知道昙媚在想什么,她的身姿倒映在水面上,有如一抹行走的彩霞。
于是,百般思量后,昙媚最终选定北魏和平年间昙曜高僧主持开凿的一个大洞窟,很快延请工匠,着手开龛事宜。那个时候,昙媚选定的大洞窟内的主尊释迦牟尼已经端坐了40多年(从北魏和平初年算起),以悲悯的情怀,迎接着芸芸众生的叩拜。每一次来石窟寺,昙媚都会在佛祖脚下跪拜许愿,而大佛肃穆的表情、沉静的内心,似乎在无声地召唤她完成内心的宏愿。
经过细致的构思、绘图和雕凿,石质坚硬却细腻的砂岩上,从此留下了昙媚对佛祖的虔诚和礼敬,也留下了她对人间安泰的美好憧憬。能在那样一个伟岸的洞窟内开龛造像,昙媚觉得此生无憾。造像结束后,她又请来一位书家,把自己开龛造像的初衷和宏愿说与对方,代请写就一篇造像记,由石匠镌于一块方形石板上,嵌在了佛龛旁的石壁上。
然而,某一天,昙媚开龛造像的洞窟,窟前石壁訇然崩坍,在让深隐在洞窟内高大的释迦牟尼坐像显露人间的同时,也将包括昙媚开龛造像在内的所有前室石雕毁于顷刻。
已经无法想象那是一次怎样的山体崩塌,也无法想象那些用心血雕凿出来的石刻艺术,刹那间便成了碎石。公元1956年11月,西北风烈烈地扫过武周山的崖壁,衰草起伏,大地即将被寒冬笼罩。就是在那个季节,考古工作者对云冈石窟部分洞窟进行了一次窟前勘察作业,在整修现今编号第20窟(著名的“昙曜五窟”之一)窟前地面时,于土层中发现了一块方形石板。工作人员随即将石板上的泥土小心翼翼地拭去,清晰的文字霎时映入眼帘。
经专家测量,石板纵30厘米、横29厘米、厚6厘米,平面近似正方形;石质为细砂岩,其上纵向阴刻文字10行,每行最多12字;石板除四角稍有缺泐外,大部分保存完好。朔风扑面,但考古人员已忘掉了寒冷,都迫不及待地辨识起了石板上的文字。辨识完毕,人们已经大概明晰了这段文字的意思,依据“比丘尼昙媚造”的落款,专家将石板上的文字命名为《比丘尼昙媚造像记》。这便是当年昙媚在武周山开龛造像时的题刻。
从北魏景明四年镌刻,到后来洞窟前的石壁崩塌,再到二十世纪中叶的1956年出土,《比丘尼昙媚造像记》题刻在黄土中沉睡了1400多年。1400年沧海桑田,北魏王朝早已成为留在史书中的一个悠远背影,时间将太多有关那个王朝的讯息隐没,但一块题刻弥足珍贵地留了下来,与之一道显露人间的,还有昙媚在千年以前许下的宏愿。
纵观《比丘尼昙媚造像记》,以魏碑体镌刻,且属于魏碑中用笔以圆为主、结构雄浑宽博的一类。国学大师康有为对魏碑有过极高的评价,为其归纳出“十美”,其中一美曰“结构天成”。与《比丘尼昙媚造像记》题刻相对,在深深感动于这份不加修饰的“天成之美”时,又遗憾无法知晓当年系何人为昙媚撰文、丹书,又是何人镌刻。
后世已无法考证昙媚是一位怎样的佛门女弟子,而她的容貌,更是脑海深处的一个想象,但她在北魏景明四年春天留下的一块造像题刻,却是虔诚佛心的见证,像一段嵌于山崖之上的记忆,记录了一位出家人面向佛祖时的那段涤荡人心的往事。她留下的造像题刻,成为后世眼中的“魏碑神品”,引人长久观瞻,而当年的佛心与禅境,幻化出了让世人憧憬的美,为所有的爱与善良,注入不竭的泉源——世界因之祥和、安宁。



ABCD_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