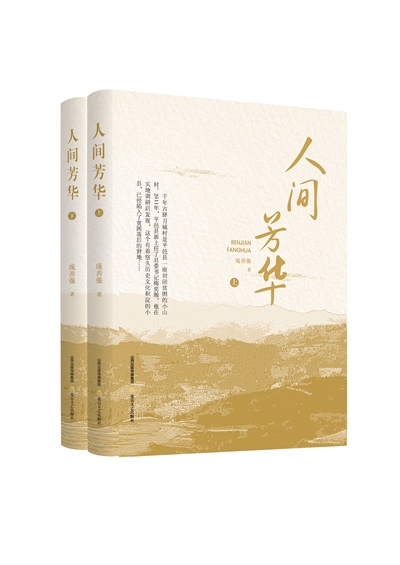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庞善强 著
众人听罢一阵大笑。石磊蹲在角落里说:“就这穷光景,你们也笑得出口?唉,受苦也是穷,不受苦还是个穷,不如每天坐在太阳地里晒暖暖哩。”
陶利伸出一根手指猛戳一下石磊的脑门:“哭丧脸好看吗?要是都像你这么懒,人人都得去喝西北风。对了,你再不干活,当心你那媳妇曹花跟着别人跑了。”
“跑就跑吧,她跑了家里还省了一个人的口粮呢。”
陶利问:“听说咱们县十多年前就是‘小康县’了。谁知道,啥叫‘小康县’?”
庞炳元说:“我也不是太懂,大概是说咱们老百姓吃、穿、住、行和医疗、教育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比方说,你家想吃肉就可以随便吃,你想换件衣服可以随便买,至于家里的住房、看病这些问题也不用再担心了。”
陶利噘起嘴响亮地吐了口唾沫:“原来这就叫‘小康县?有肉吃,还有新衣服穿?在咱这里分明是白日做梦!”
庞炳元叹息一声:“唉,春生所唱的是醉话,其实也是大实话。自打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虽然说咱们村民现在的生活的确比过去好多了,最起码人人不饿肚子了。但是,我们哪里到了什么小康。咱们村80%以上的村民们还挣扎在贫困线上。眼下我们不光是吃水困难,村民们住的还都是危房。自打这村委会从后边的庙院搬到前面这排平房,那么好的一处庙院也倒塌了,戏台也塌架了,那可是明代的建筑,多可惜。”
“我们自己住的家都顾不过,谁还顾及得了庙院。这自古贫困,贫的是没钱没势的,困的是木头一样呆头呆脑的。你家再贫困,还有亮堂堂的3间新瓦房,我们有什么?”
庞炳元一听陶利的话,顿时面红耳赤。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谁都知道我家盖的那几间房,靠的是两个儿子在城里省吃俭用做买卖,否则我不是和大家一样住乱窑洞。”
陈志远挤在人群中搭了一句话:“老支书,为啥咱们村一直脱不了贫?”
庞炳元回头一看,是陈志远,这个敦敦实实腼腆的小伙子,总是让他有一种莫名的喜欢。庞炳元摆了摆手说:“实孩儿,你过来,过来这边站。以后不敢再叫我老支书,都不当好多年了。”
陈孝安说:“这实孩儿有出息。如果人人都像他这么有骨气,也不至于能穷到哪里。”
庞炳元说:“咱们村的穷根子由来已久,自打天户山的官道被废弃,咱们村就再没有过一天的好日子,一直被封闭在这大山里。改革开放前,大家伙儿是一块儿穷。那年月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咱老百姓虽然经济困难,却精神头十足。1983年咱们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集体耕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咱们村过去的精气神慢慢地变了,个人算计多了,这种情况怎么能发家致富。”
马二女牵着福蛋儿的手说:“照你这么一说,还是过去农村大集体好?”
庞炳元说:“我说的不是这个理。社会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大集体的时候你能这样逍遥自在?你能撑圆了肚子在街上乱圪转?显然不能。国家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没有错,但是耕地分开了,咱们人心不能分离,精气神不能丢。这基层的干部一旦丢失了责任心,那整个村子就成了一盘散沙,这就好比一个家庭,作为家长成天不务正业,你说这孩子能有一个好?俗话说,没有领头羊,独闯喂了狼。领头羊的作用就是引领方向,即便是路上有陷阱,先丢命的是他自己;如果遇上了岔路,他会凭经验做出正确选择;即便遇上了狼,他也会第一个冒死去迎接挑战。所以说,没有好的基层村干部,村民们别想走上致富路。”
马二女说:“老支书,村干部不称职是咱村致贫的一个原因,你和陈孝安村长搭班在咱村也干了13年,咋咱村的老百姓还是一直那么穷?”
庞炳元看了一眼陈孝安:“以后大家别叫我老支书了,已经不当好多年了。你谈的这个问题,让孝安给说道一下。”
陈孝安说:“我和炳元在咱们村担任了十三年的村干部,虽然没有带领大家脱掉这身穷皮,但是我们付出的辛苦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大家也是亲眼见过的。分产到户后,那时全村耕地的平均亩产量不足一百五十斤。我们接手了村里的摊子后,再三向县里申请,打了两眼机井,但是在勘察定位上出了问题,那井抽不了多长时间就没水了,实际利用价值不高。不过,就凭这样的两眼井,一部分耕地的亩产量比过去翻了一番。全村原有耕地五千四百亩,后来退耕还林占去了一千五百亩,但当时是退地不退税,减产不减费,农业税还得按照原有耕地的面积进行摊派,村民们的负担更重了。万般无奈,炳元和我四处取经,想带动村民们发展副业,这事却最终没有闹成。”
马二女说:“要是大家都像我姑父一家,坚持把那黄花种下来,或许这日子就好过多了。”
“咱村有句老话说:穷死不离月城,饿死不种黄花。月城村自古就是一块风水宝地,所以千百年来,咱村的先祖们一茬一茬把最后的一把骨头都留在了这片土地,就是再穷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如今世道变了,月城村再拴不住年轻的一代人。大家应该没有忘记,咱村的黄三爷是怎么死的,当年就是因为他种黄花菜丢了性命,咱月城的村民才彻底断了种黄花的念头。虽说那是发生在过去年代的事了,但毕竟种黄花没有那么容易。且不说咱村地里没有水源,现在劳力、蒸馏用的煤炭、晾晒场地等,这些都没办法解决。土地分开后,黄炳福咬着牙坚持种黄花,一来他是在弥补对父亲的亏欠,二来他煤矿上有个当官的亲戚,能弄上煤炭。”陈孝安说。
“那你们为啥不带着村民继续干下去?”马二女又问。
庞炳元叹息一声:“唉,没办法,干不下去了。我们都老了,压力又太大。村里通往外面没有一条像样的路,生产物质运不进来,农产品又运不出去;耕地没有水源,难以发展农业生产,群众的观念不改变,发展不起来新产业;村委会没有钱,咱不出去,就没人支持咱们村的工作。加上当时咱村民的负担太过沉重,什么‘三提五统’,包括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业税、计划生育管理费、计划生育罚款、乡村两级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军烈属优抚费,乡村道路维护费,学校里的煤电费、代课教员的工资,五保户的养老费用,接待各级部门工作消费等等,这些费用都得从咱村民们的血汗中一点一点往出抠,我们真的没办法干下去了。”
这时,旁边一户人家的大门“吱扭扭”打开一道缝,满头白发的马建忠探出头向人群这边看看,然后故意倾下身来降低自己的高度,他面带微笑向众人点了点头,便又赶快缩了回去,大门“咣当”一声被关上。
陶利说:“这么多年了,这人还是贼眉鼠眼的。”
“老马应该是个好人。大家不要抓住他的历史污点不放,老马在咱村一待就是近四十年,谁见他做过偷鸡摸狗的营生?”庞炳元说。
“他最擅长的就是伪装了。当初,他被下放到咱们村接受劳动改造,一直装聋作哑,后来突然间开口说话了,这样的人谁敢相信?”
“那时,他是被吓出的毛病,后来好了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咱们不要议论人家的长短,还是说说自己。”庞炳元说。
马二女说:“要是现在的村干部能像老支书当年那样,一心想着群众就好了。”
“村干部不想群众,有人想着你哩。”左春祥嬉皮笑脸地说。
“你胡说什么?小心我撕烂你的嘴!”马二女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陈大勇低下了头。
“你们看,马二女害羞了。”左春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