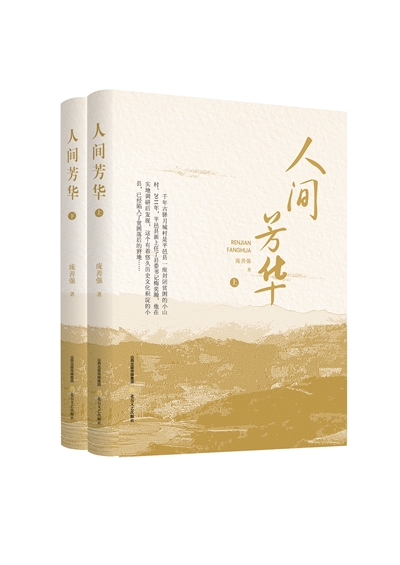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庞善强 著
“古家庄人民公社党支部在河堤上临时成立了几支共产党员先锋突击队,大家在河堤上向党向毛主席庄严地宣誓后,便分到各个危急的堤坝口进行堵漏加固。那会儿缺少机械设备,咱们公社除了两台行动缓慢的推土机和几台破旧的‘铁牛55’拖拉机外,所有的抢险工作都得依靠人力。我们党员突击队在河堤上连续坚守了两天两夜,总算是安全守住了堤坝。在我被替换下来的时候,才感觉到腰椎下方疼得厉害,用手一摸,起了一个大疙瘩。我猜想,一定是被河堤垮下来的石头砸了腰,结果回家后,我再下不了炕。我个人的疼痛算不了什么,可万万没有想到,9月9日,晴天霹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永远离开了我们。村里的大喇叭响起追悼会的那会儿,我忍着剧痛爬出了街门,眼瞅着全村的人流着泪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缓缓送行,我却寸步跟不上,我不中用啊。”
庞晓武说着,眼泪滑落下来。
梅奕瀚掏出一张纸巾递给了庞晓武。
“那后来呢?”梅奕瀚低沉地问。
“后来这腰椎竟然慢慢不怎么疼了,我也能下地走路。彩霞生下二云那年,我的腰疼病又犯了,一天比一天厉害,不得不去医院查了一下,人家说腰椎管错位压迫到神经上了,再不动手术恐怕两条腿要瘫痪。咱家哪里有那个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这30多年下来,我一直依靠止疼药过日子,只是这腿一年比一年细了,没有了一点力气,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只能凭这双拐勉强走路了。”
梅奕瀚痛楚地说:“老哥,你这病拖得太久了,恐怕已经治不好了。”
庞晓武看了看自己的腿,他叹息一声:“唉,我知道我的腿治不好了,这毕竟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是,这基层党支部再治不好,民心就完全散架了,老百姓哪里能有好日子过。”
庞晓武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却在梅奕瀚的耳边炸响了一个雷,他猝然又是一惊。
“老哥,请你再说道一下党支部的事。”
“就算是石头缝的蚂蚁还有一个分工明确的组织系统,天空飞行的大雁也有一只领头雁。过去,为啥众人能一条心,就是因为有一个与群众穿一条裤子的党支部。那时候,人们说干部和群众是鱼和水关系,基层干部大小事情都与老百姓的心思连在一起,群众虽然贫穷,但是彼此间没有高低贵贱,没有怨言和矛盾,大家有劲儿就往一起使,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很高。后来,政策放开了,时代也变了,慢慢地什么都在变,所有的人和物都变了,包括干部、党员、群众、亲情和村庄。”
庞晓武说到这里,调整了一下坐姿。他接着说:“而现在,这基层干部和群众变成了一锅汤里油和水的关系,你从表面去看是红红火火,是有滋有味的一大锅。但实质上,上面浮动的永远是一层油,而下面却是老百姓清汤寡淡的一锅水,彼此间隔开了一条界线,所有人的心里只剩下了钱的概念。干部们为了钱,只知道挖空心思捞取个人的利益,基层党支部变成了一个沤底塌帮空空的筐子,而党员们则成了一粒粒随风飘散的沙。每一粒沙子都被磨得没有了棱角,变得越来越圆滑、自私而现实,只盯着自己家里的柴米油盐旱涝收成。可是,这些年村里人越盯变得越穷,越盯变得越迷茫。一批又一批的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离开了村庄,甚至脑子比较活泛的中年人也都走了出去。房子没人修了,老窑洞一间又一间倒塌了,现在这村子死静得有些可怕。”
梅奕瀚的脸上不禁火辣辣的,像是猝然被人扇了一个响亮的巴掌,他只感觉心里一下子堵得慌,过去所有的美好印记竟一下子模糊起来。他掐了掐脑门,努力调整着自己的状态,但依然有一阵紧似一阵的疼痛钻入心里。
面对眼前这位曾经钢铁般的优秀共产党员,梅奕瀚一时不知该如何说服自己,更无法去直视他此时那双失落而无望的眼睛。
过了一会儿,梅奕瀚问雷彩霞:“你们家现在种多少亩地?”
“咱这村子那地也不叫个地,很多地都撂荒了,我们种了有三十多亩地,除了留下家里的口粮,一年卖不了几个钱。”雷彩霞说。
“你家一年能收入多少钱?”
“咱们这里的耕地是旱地,靠老天爷吃饭,瞪眼瞎忙乱。庄稼长不成好苗子,产量上不去,辛苦一年只能收入几千块钱。再扣除种子化肥,更剩不下几个钱。这么大一家人,种地要用钱,看病要用钱,更不敢想给孩子们娶媳妇的事。你看看,这窑洞都快塌了,家里没钱,想翻修一下没钱。”雷彩霞无奈地说。
梅奕瀚进屋仔细查看,迎面是灶台,其上摆放着半盆吃剩的玉米面糊糊,那糊糊已经干裂开一道口子,黑乎乎的苍蝇密密麻麻爬在裂口上正吸食。屋子里陈设极其简陋,炕上铺一块褪了色的人造革油布,几张陈旧的薄被子折叠起来堆放在后炕角落,地上靠墙中间摆放着一个漆色斑驳的小衣柜,衣柜的两边各放一口黑釉大瓮,衣柜上是一台老旧的小电视,在东西两面的墙壁上果然有两道明显的裂缝。
“小魏,回去后将这里的实际情况尽快汇报到省里,看看能否争取到扶贫款项。住房的事耽搁不得,这随时会危及群众的生命安全。”
“好的,我回去后立马起草报告。”
梅奕瀚说:“老嫂子,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辜负了大家的厚望,对不起了。”
梅奕瀚知道,面对如此贫困的人民群众,此时此刻无论自己做什么说什么,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
二云依旧趴在窗户上,见梅奕瀚打屋里出来,便再次行了军礼:“首长辛苦了!”
梅奕瀚叹息一声:“唉,多好的青年,竟这样毁了。老哥老嫂子,不能再这样把你儿子关在屋里,这是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雷彩霞说:“可是,把他放出来,他会胡乱打人的。”
“小魏,回去后与县人民医院联系一下,让他们安排专人接二云到医院给予积极治疗,尽最大的努力把他的病情控制住。”
“好的,梅书记,我会安排好这件事情。”
梅奕瀚刚出了庞晓武家的院子,打南面跑过来一群人,跑在前面的是一个穿着破背心和一条裤衩愣头愣脑的小伙子,后面跟着一个拎棒的老汉和一群看热闹的村民。
就听得有人喊:“傻三,别跑了,你家的老母猪还在等你哩。”
那老汉回过头骂了一句:“我看你也是个牲口!”
一群人闹哄哄地来到了梅奕瀚的跟前,那傻三竟然躲在了梅奕瀚的身后,嘴里还“嘿嘿嘿”乐着。
“这位是刚调任咱们县的县委梅书记。你们这是干啥呢?”魏悦问。
“县委书记?”众人便呼啦一下围了上来。
“梅书记好。”
梅奕瀚定睛一看,有些意外,面前的女孩竟然是黄雅萱。
“你是这个村子的?”梅奕瀚附在她耳边大声问。
“是的,月城村的。”
“噢,我想起来了,你爹说过,你们是古家庄乡的。这老人拿着棒追赶这个小伙子,为什么?”
黄雅萱的脸顿时羞得通红。
左春祥嬉皮笑脸地说:“这傻三发情哩,到处瞎祸害。”
“你说啥?”魏悦严肃地盯视着那人。
“我没瞎说。这傻三近来经常祸害家里的鸡、猫,今天又祸害家里的老母猪。”左春祥认真地说。
“你还敢胡说!”魏悦不禁恼怒起来。
“老人家,你为啥打他?”梅奕瀚问。
那老人丢下木棒,叹息一声,然后低着头灰溜溜地走开了。
庞炳元说:“我曾经是这个村的支书,左春祥说得没错。”
“那好,你来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梅奕瀚说。
“刚才走的那个老汉是傻三的爹,叫庞极无,也是这十里八村有名的老铁匠。说起来,这事怪不得傻三,也怪不得庞极无,是咱村这穷光景把人逼成了这个样子。”
庞炳元说着,用手一指:“梅书记,你看,这就是咱村的现状。就是这么破的窑洞,一个家庭也只有三间。那些年,家家户户最少四个孩子,很多家庭都是七八口甚至是十几口人,是老的老小的小。你说,这三间土窑洞怎么住?只能是全家人挤着睡,就算是女婿登门,也只能是和丈母娘一条土炕睡。庞极无家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包括这个最小的傻三。那时候,他家五个女儿和爷爷奶奶挤在一条炕上,庞极无两口子和两个儿子睡一间屋。人啊,就算再穷,但生理上的那点需求还是避免不了的。一条炕上睡,天长日久了,难免孩子们会在夜里看到家大人的那点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为啥过去农村里的强奸案频发,一方面是因为家里穷,男孩子娶不上媳妇,而最重要的是家长们的那点事让刚刚懂事的孩子过早地成熟,甚至因此变得心理扭曲。傻三哥哥就是因为这事,打懂事后就不愿意再和父母睡,他宁肯和村里的老盲人三明子去做伴。庞极无总以为傻三是个傻子,所以他平时夜生活不太在意,有好几次傻三将他爹从他妈的肚皮上给拉了下来。等傻三长大了闹出了乱子,他才后悔不已。傻三虽然是个傻子,但他毕竟比一头猪要聪明,他也有生理需求,所以经常骚扰村里的妇女。傻三被人一次次暴打后,似乎也懂得了什么,但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家里的鸡、猫、羊的身上,这不今天他又去强奸他家的老母猪。唉,一个穷字,把一个傻子都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