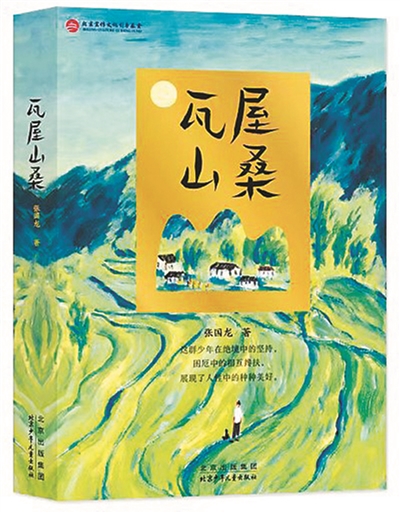一位作家最幸运也最成功的标志,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形成自我标识性的创作风格与文学身份。这需要一些艺术的直觉、敏感,更需要作家持之以恒的努力以及对艺术的绝对忠诚。张国龙对四川乡村少年的书写已经颇有一些积累,他坚持不懈地写,无功利地写,终于开花结果,越写越好。透过他的探索与实践,我们能够对原创儿童文学,特别是少年文学的艺术新变获得一些深刻的启示。
张国龙的写作姿态,首先引发我们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作出真诚的反思。毫无疑问,文学的根是生活,生活是文学唯一的源泉。写作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是由对生活的立场和态度决定的。文学的出发地与归宿地只能是鲜活的、原生态的生活。如果说创作没能形成崭新的面貌,那我们首先要追问,是不是自己的生活观出了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恒定的路径只能是在生活现场,始终秉持实践论的美学观念,关注并写出人民的喜怒哀乐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尊重并投入生活显然比艺术技巧更为根本,特别是在当今人工智能参与现代人生活的当下,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是独一无二的作家灵魂究竟能为文学赋予什么。张国龙的文学信仰立在广袤的民间大地上,特别是他生长生活的那块土地上。他将“生活”作为写作的中心与主体,在文学与生活之间始终建立起赤诚的情感联系,而且将追求写透生活、让生活留史作为至高的艺术目标,他的创作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他在用实践回答文学究竟“为了谁”,以及“如何为”的问题。
持之以恒地写生活,便能写出生活的味道,写出生活的品质。《瓦屋山桑》较之作家此前的同类题材创作,显然笔力更自然雄健,生活与艺术的质感浑然一体,观照、介入、反思现实更练达通透。作品一如既往地聚焦成长,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传统,重视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处理。作家以火热的生活激情打底,但以冷静、节制的笔致去触摸生活的本相,遵循生活自身的规律去探知人生的答案,而不是随意、想当然地附会作家的意图,这应该也是张国龙对生活始终持敬仰态度的结果。所以他笔下的人物能够活起来,人物强烈的主体性得有托底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来自生活实践的那股永远充沛的力量。《瓦屋山桑》有中心人物,但也有人物群像。群像塑造是儿童文学成长内涵书写的必然构成,它在积极面对少儿与生活的多元现实命题,群像愈饱满愈显示生活的复杂性。
为少年代言,将少年的生活置于高度的文学关怀中,这是儿童文学人文精神的核心体现。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使得张国龙从感性到理性,对文学表达世界、表达自我的特殊方式认识非常深刻,尤其是对成长书写的艺术理解与使命践行,他在国内儿童文学界是居于前沿的。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生活的一种调理,它基于生活素材要对人生作出审视,彰显存在命题并作出价值选择与价值建设,儿童文学的文类特质及其功能尤其决定了它面向生活的立场与态度,以及最终给出答案的角度与方式。写给少年的文学体贴关怀少年的成长境遇,它以文学的方式将少年读者带入不同的生活场域,与作品主人公发生深度共情,集中、有秩序、有深度地对生活作出全面的体验与检视。最根本的是它要突破日常生活的琐碎,直面生活的复杂性并从中提炼价值命题,引导少年自主参与并作出理性判断,儿童文学从本质上看为儿童提供的是朝向生活实践的方法论,当然其内核是应对生活的巨大精神能量。张国龙的写作在这一点上是自明的。
近些年他以系列写作的方式,以浓厚的历史意识关注乡村少年的精神成长,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乡村少年这一群体的成长与社会发展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些年来儿童文学界对此领域多有探索与艺术表现,张国龙在此领域也已经比较清晰地形成了自己的方向与写作理路。他的写作不是一时一地、从外部进入的方式,而是持续聚焦自己的故乡、以自我深切的情感体验为基础、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看山乡巨变中乡村少年的人生轨迹。我觉得他为乡村少年写作最大的价值不是高高在上地、先在地给出某种想当然的方案,而是在乡村生活自身的逻辑里,从生活内部清理出必须面对的现实命题,以中心人物的心理与行动再现为轴心,以其他人物多样化人生经历为呼应,在情感与故事的审美张力中渐进浮现乡村少年成长必然面临的关键命题——就是“走出”还是“坚守”的两难选择。这个问题看似是个体的,但其实它直接有关于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发展问题。从乡村建设主体这一层面看,这与少年人的身份认同、觉醒的主体性、责任使命意识、中国伦理精神等多个维度都紧密相关。其中存在很多矛盾与悖论,张国龙的写作目前对此充满着浓厚的问题意识,也有深刻的反思性,特别是呈现出典型的中国式情感样态,就是对“家”与“家园”的固持与守护立场。
乡村少年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命题,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儿童文学界可为、必为的空间非常大。希望张国龙从历史出发,始终紧跟时代,以“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评价标准,在该领域继续深耕劳作,推出更多直面现实真命题、呈现时代新气象的精品力作。
据《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