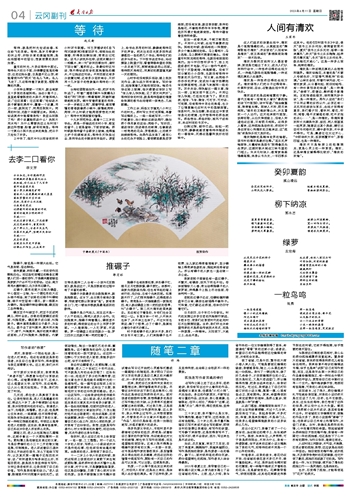写作者的“热爱”
那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一位老人打来的。他在电话里说是我的读者,并且自己也喜欢写作,很希望能与我见面聊聊文学。这之前,我们并不相识。
对于爱好文学的朋友,我常常是“来者不拒”,很愿意与他们分享彼此的心得。在喧嚣浮躁的当下,还有人这么渴望谈文学、谈写作,实在难得,让人从心里无法拒绝。于是,我们约定了时间。
几天后,那位老人果真到了我单位。让我吃惊的是,老人已是耄耋的年纪,将近九十岁了,身子骨硬朗(在电话里,我并没想到问他的年纪)。我请老人坐下,先喝茶,再慢聊。老人说,他是乘公交车来的,一路颠簸,但不觉得劳顿,而是快言快语地说之前读了我的文章,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听到这么高寿的老人的鼓励,说实话,我真有些羞惭,自己实在并非老人所言那么优秀。
寒暄之后,老人从包里掏出几篇稿件,还顺手拿出一个大剪贴簿和一本书。剪贴簿上是他曾经发表过的文章,书是自费编印的小三十二开的散文随笔集,印制精美。老人详述着自己退休后怎么开始迷恋读书,怎么下笔练习写作,以及某天第一篇稿子见报后的兴奋,说:“你知道我为啥身体这么好,耳聪目明的,就是因为我坚持读书写作,文学让我老有所乐,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写作是我活着的动力。”老人说着,眼睛里不时闪现着兴奋的光芒。说到动情处,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绢,擦擦眼角。这个擦眼角的动作,让我无意间看到他的一股可爱劲儿。在这样一位醉心于文学的老人面前,我能多说什么呢,似乎只有聆听了。
我边听边翻看老人的剪贴簿,心里估摸着,老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生,可不就是九旬的生命历程了!这长长的一生,他经历了多少的风霜雨雪,这些文章也许只是他晚年闲暇时光的一些感悟吧。每一篇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他都剪下来保存,还标注了日期,我被他对文学的这份热爱而感动。老人一边说写作,一边给我讲他和老伴晚年的天伦之乐。说心里话,老人的那些已经发表的文章其实并没有多少新意,只是一些生活的随感,但面对这样的老人,怎么能对他的文章妄加评论,又怎么能对他不生出敬意呢!他如此高龄,忍受长途颠簸,来找一位陌生人聊文学,还带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因为心底的热爱,才对我有了这份信任。我想,这就是写作者内心对文学葆有的执着吧,而这份执着,无关作者的出身与年龄。
告别时,老人在自己的书上给我留言,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对一个近九十岁的人而言,写那么一小段话或许并不是件轻松事,但他却没有丝毫的潦草。由眼前的老人,我想到了我自己。
十一二岁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把在报纸上读到的好文章剪下来也制成剪贴簿,虽然那时的我并不懂什么是好文章,对于文学,只是朦朦胧胧喜爱,但正是这份朦胧,引燃了我心底对文学的热爱。当我不断接触文学书籍并尝试着由写日记开始把心灵感悟打磨成一篇篇短小的随笔后,我才明白了这份对文字的热爱正是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并一步步走近文学,与写作相伴。
后来,我把自己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整理出来,满怀憧憬地寻求出版。尽管在当时的状态下我已经足够用心,但作品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面对读者的鼓励和夸赞,我想得最多的是自己写作能力的欠缺,以及常常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浮躁。不过我又想,正是因了对文学的这份热爱和执着,这么多年,我从未停止过写作,从未想到要放弃,尽管我的不少文章并不能称之为“作品”,而仅仅是练笔,但我一如既往地写,并渴求着更大的进步。
很多热爱文学的人,年轻时差不多都曾有过相似的经历,那便是:试着给自己喜欢的作家写信,热切地表达对文学的痴情,倾吐学习写作的困惑,而且渴望能收到回信。还有人恨不得集全偶像作家所有的文集,一本接一本读,在书里品咂作家的喜怒哀乐,甚至憧憬其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然后在这样的憧憬中提笔写作,期盼有一天自己的作品可以发表,可以出版。这便是热爱。
热爱,一个从骨子里生发出来的词汇,对任何人而言,这是生之幸运,是体现人生价值的源泉。有了这种热爱,并且坚持向前,生命路上会收获不一样的景致。
孤独是写作者灵魂的修行
在写作之路上走了这么多年,坦然地讲,我没有写出过什么像样的作品,虽偶有文章发表,但都是“小打小闹”,不足挂齿。身边的作家朋友,不断写出有分量的作品,说实话,我心里羡慕,也曾眼红,但平心而论,“爬格子”这事,还是靠“天分”,得开窍,得忍受孤独,坚持而为。
三十岁之前,我不懂什么是文学,写作靠热情,感动了便写,过后再读,实在有些勉强。三十岁之后,我尽量不触碰自己写不来或不适合写的题材,即使当时的场景让我感动,有写作的欲望,可冷静下来细想,还是觉得我写不了,也写不好,便不去尝试,因为,写出来也是不成功的。
如此,反反复复,肯定了又否定,否定了再重来,踽踽独行,我越来越明白,写作是孤独的跋涉,是热爱者一生的修行。静下心,面对纸和笔的那份沉寂、那份渴望倾吐的孤独,写作者本人体会得最深。
2015年春夏之交,我带着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文稿,从晋北故乡踏上了去往省城的列车。之前,经人介绍,我与省作协的一位文学编辑取得了联系,希望请他“看看”我的这部小说,或者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这位编辑的肯定,并有机会发表。
到了省城,已是午后,繁华的大街小巷人来人往。可能是要面见编辑的缘故,我顿感紧张,随之,心头莫名地升起一份孤独。我叫了一辆出租车,绕了好几条巷子,才找到编辑所住的小区。因为是初见,又是大老远登门,所以编辑很热情,把我当远来的客人,给我切西瓜吃。吃过瓜,我便递上了自己打印装订好的小说文稿,厚厚一摞,心里有些忐忑,更有期待。原来,希望得到别人肯定或赞许的滋味,是那么复杂,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从进门落座,到编辑简单询问了小说的主旨和故事梗概,不过十几分钟,就没再往下谈。我起身告辞,不多打扰,毕竟,我是来投稿的,不是串门儿,但我多么渴望编辑能就我的小说多谈那么几句。
走出小区大门,我像了却了一个心愿似的,坐在路边的椅子上,长长地舒了口气。眼前,车来车往,人声熙熙,可于我是那样陌生,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虚脱感,似乎送来的这部小说文稿耗蚀了我的元气,而等待的却不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时值春末,在我的故乡,春花仍在开放,但省城的春花差不多已开尽,绿叶蓬勃起来。不过,我所坐的长椅对面的花圃里,有一株榆叶梅却正开着粉色的花朵,且是新绽放的。花瓣微带香气,娇俏而惹眼,在其他花树都走向季节深处的时候,它却开得饱满,似乎想要把春天留住。
与眼前这仅剩的春花相对,我心头的那份孤独感骤然浓重起来。置身偌大的省城,我突然觉得我和那花儿有些命运相同。我来给素不相识的编辑送书稿,似乎也是来“试探”自己的写作前程,而且,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将自己的作品拿给编辑指正,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儿,更想给自己的辛勤付出寻一个交代。榆叶梅寂静开放,艳丽而有些高傲,可我的心却五味杂陈。
返回故乡,过了很久,那位编辑才礼节性地给我回复,对我的小说仍然只是泛泛说了几句,自然,也不乏鼓励。其实,这长长的等待,我已想到了这样的结果,所以没什么太大失望。事后看,我那部小说并不成功,甚至有些拿不出手。对省城的文学编辑而言,接触的作品太多了,我的小说显得“寒碜”了些,但我却以自己未有之热情写作,并登门求教。当时,我确实是那样的热情,心中抱着无限的希望。想起省城街头那株独自开放的榆叶梅,我曾有一种跟它一样的孤独感,但还是放下了心中所有的期待,与昨日告别,继续往前走。
人在时间之河跋涉,不气馁,不焦躁,忍受必要的孤独,我想,这应该是生活的一种姿态。独自绽放的榆叶梅,或许孤独,不及群芳争艳时的花团锦簇,但它开到了最后,孤独反而成就了它的美。写作者也一样,与文字结缘,便开始了漫长的孤独之行——是灵魂的,也是肉体的。
也许,忍受得了孤独,才能等到笔下“花开”的那天。